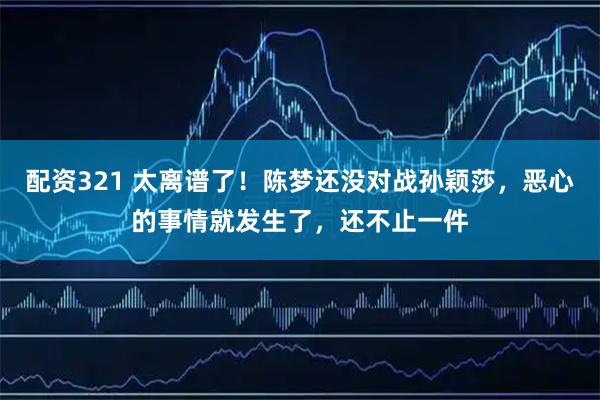在回忆1948年辽沈战役中的长春战役时,郑洞国,曾任国民政府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和代总司令,表达了深深的悔恼和愧疚。他说:“每每回想起长春围城的惨状,心中总是不禁感到心惊肉跳,尤其想到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,我痛苦万分配资321,终生都难以对长春的父老百姓交代!”
郑洞国是黄埔军校一期的优秀毕业生,早年便参与过东征北伐,抗战时期他更是屡战屡胜,战功赫赫。无论是在保定会战、台儿庄大捷,还是武汉会战、昆仑关大捷等战役中,他都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。战后,他还曾担任远征军驻印新一军军长,带领部队收复缅北,扬名海外。然而,尽管他经历了无数的战斗和生死场面,是什么让他对长春战役记忆犹新、终生难忘呢?
展开剩余78%要弄清楚这个问题,我们可以从当时的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的回忆中找到答案。在他晚年的回忆录《长春困守纪事》中,尚传道描述了当时长春的悲惨局面:“开始强行疏散人口时,很多市民死于饥饿或疾病,他们尸骨遍地,呻吟声不断,场面如同人间地狱。到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时,因‘杀民’政策以及饥荒,死亡的长春市民共达12万人。”这12万人的死亡,让人震惊不已。
与辽沈战役中我军和国军的伤亡数字相比,12万人的死亡无疑是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数字。辽沈战役历时52天,我军的阵亡人数约1.4万,伤者5.3万,而国军的伤亡合计约为5.5万人。相比之下,12万的死亡数字显得尤为惨重。尤其要注意,长春的死亡人数几乎是辽沈战役中的总伤亡人数,这也突显了长春人民所遭受的极度苦难。
长春曾是东北地区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,1945年抗战胜利时,长春的市区人口约为50万。但随着国共对抗加剧,大量国民党人员和恶霸流入这座城市。到1948年初,长春人口逐渐减少,至1948年5月30日,长春人口已减少到约40万,其中包括10万国军家属和留守人员。随着四平的解放,长春与沈阳的联系被切断,导致了又一波人口逃亡高潮。
郑洞国于1948年3月上任,5月30日长春被围之前,他已经储备了大量粮食。据估算,长春的存粮能够支撑到7月底。但进入8月,粮食将告罄。为确保军队的粮食供应,蒋介石于6月发密电要求郑洞国将老百姓的粮食收归公有,并由政府统一发放。时任长春市长的尚传道反对这个做法,认为这会造成市民的骚扰和贪污。最终,他们采取了折中的办法:“战时粮食管制办法”,规定市民存粮的数量,余粮必须上交,供军队使用,市场的粮食价格也必须由政府统一管理,严禁哄抬物价。
然而,尽管有了这一措施,粮食市场却陷入了混乱。商人囤积居奇,价格飞涨。为了严惩投机行为,郑洞国下令枪毙了几名商人和军官,但对上层军官的投机行为则选择了视而不见,显露出他无力解决根深蒂固的军中腐败问题。
与此同时,郑洞国还面临60军与新7军的争斗。60军的士兵因为粮食短缺,开始强行抢夺市民的粮食。这样一来,长春市民的生活更加艰难,连家里的炉灶和房梁都成了军人们的燃料。随着粮食紧张,公园、马路上的树木被砍伐,墓地的棺材也被挖出来当做柴火,城市的面貌迅速荒废。
在此危急时刻,蒋介石下令将市民疏散,以减轻守军压力。郑洞国只得按照命令执行,他下令将无法存粮的百姓强行赶出城外,并指定军警按人头将他们赶出。数万名长春市民被迫离开家园,滞留在长春城与我军封锁线之间的“死亡地带”。蒋介石将这些百姓当做“包袱”甩给我军,企图将责任推卸给解放军。
然而,蒋介石的这一阴险手段给我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在长春战役的围困中,解放军决定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。地下工作者杨滨提出,将难民接纳并安置在解放区,给予他们救济,能够有效瓦解国民党的军心。此建议被迅速采纳,解放军向难民提供粮食和生活必需品,尽力保护这些无辜的百姓。
与郑洞国的无奈和蒋介石的冷酷相比,解放军的做法则显得更加有人道主义精神。虽然面对同样的局面,郑洞国与我军的反应截然不同配资321,但这一切都让郑洞国在晚年仍对长春的百姓心怀歉疚。通过这段历史,我们看到了战时民众所遭受的巨大苦难,也更理解为何郑洞国在回忆起长春战役时感到深深的痛悔。
发布于:天津市美港通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